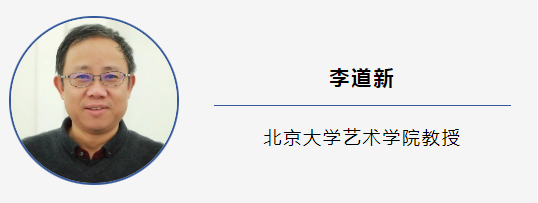
提要:《平原上的火焰》是一部“罪爱电影”,但在影片主创与电影观众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认知壁垒和情绪反差。本文试图在小说原著和改编剧集《平原上的摩西》与影片《平原上的火焰》之间展开比较,探讨三重“平原”叙事同创共生之后,作为一个难得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开放文本本身所拥有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从《平原上的摩西》到《平原上的火焰》,自始至终都在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呈现敏感主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并试图暗示或揭发运行其间的系统暴力。这是“罪爱电影”的一次锐猛探索,也是国产电影在现有体制机制下寻求多方对话的一次突围尝试。
关键词:《平原上的摩西》 《平原上的火焰》 罪爱电影 敏感主体 系统暴力
在百度百科、豆瓣电影与1905电影网等各大平台,以及2021年12月24日全国公映的官方海报上,均将《平原上的火焰》归为“爱情”“犯罪”“悬疑”等相关“类型”,并以“放一把火,等一个人”或“火的约定”作为全片的宣发语;而在2025年3月8日改期公映时,此前的宣发语变成了“恨一场,狠一次”。显然,没有了“约定”,也不再“等”。
不得不说,从十年前的准备开始,经历改编、疫情、更名、删减、撤档与换角、补拍等无数“困难”和“意外”,十年后才公映的《平原上的火焰》,似乎正在褪去“爱情”与救赎以及信念的温暖底色,倾向于强调更多“犯罪”与莽然和绝望的狂暴因子。事实上,除了抢劫、打架斗殴、枪击、撞车、卡脖子、扇耳光、脑袋拍砖和强奸等各种各样的“暴力”场景之外,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能激起部分影迷和普通观众情绪的段落,便是女主人公李斐之于孙天博的“癫狂反杀”。在这里,饰演李斐的周冬雨表现出色,贡献了全片中最为血腥残忍而又惊心动魄的演技。
然而,影片在春节档尤其《哪吒之魔童闹海》之后上映,票房数据并不乐观,一些观众也对影片的叙事策略、原著改编以及版本删减等表现出无法理解和较难接受的态度。导演张骥则表示,删减的目的是让电影“更合情、更合理、更合适”,并且希望通过“更快的节奏”,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体验更加“流畅”与“愉悦”;[1]原著作者兼艺术总监双雪涛在接受独家专访时也直言:“喜欢这个利索坦荡的公映版。”[2]看起来,在主创与观众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认知壁垒和情绪反差。本文试图在小说原著和改编剧集《平原上的摩西》与影片《平原上的火焰》之间展开比较,主要通过分析其在敏感主体与系统暴力领域的异同,探讨这种认知壁垒与情绪反差的根源之所在。

鉴于不同媒介及其艺术形式的特殊规定性,改编自小说原著的网络剧集和影片文本,也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小说原著的叙述语体和精神气质,或者削弱甚至遮蔽其为读者和评论家所激赏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即便如此,从《平原上的摩西》到《平原上的火焰》,自始至终都在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呈现敏感主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并试图暗示或揭发运行其间的系统暴力。
实际上,无论在“野蛮”时代,还是在“文明”社会,暴力不仅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且似乎来源不明,无远弗届,仿若存在着一种瓦尔特·本雅明意义上的纯粹的“神圣暴力”[3]。雅克·拉康也曾指出,暴力不仅是外在的行为,更是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家庭暴力”对主体在符号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三重维度势必造成结构性破坏和整体性崩塌;当“家庭”这一本应庇护主体的符号系统沦为“暴力机器”时,主体被迫在废墟中重建自我,但治愈的关键不在于遗忘创伤,而在于重新符号化创伤机制,亦即通过语言、艺术或新的关系网络,将无法言说的实在界剩余转化为可栖居的意义碎片。在此基础上,斯拉沃热·齐泽克进一步讨论了主观暴力、符号暴力和系统暴力等问题,[4]并在相关著述中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作为一种主体的幽灵予以重申,不仅肯定一个人的特殊主体性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如女性的、同性恋的、族性的等解放作用,而且导向了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认同政治。[5]在大卫·汉森-米勒的著作中,更是将对敏感主体、性别特质与流行电影的分析结合起来,讨论“文明暴力”是如何通过“电影暴力的吸引力”而得以实现的。在他看来,“电影暴力的吸引力”可以归因于特定叙事在那些被隐藏和浸透暴力的领域中有效地重新刻画暴力的方式;而对暴力的普遍表现,可以满足一种洞察和理解原本不透明的东西的需求,也就是说,“文明暴力”总是会在流行电影的特定叙事中想象式地重新确立。[6]颇有意味的是,从《平原上的摩西》到《平原上的火焰》,竟然暗合本雅明、拉康与齐泽克、大卫·汉森-米勒对敏感主体与系统暴力的阐释路径。或许,这就是三重“平原”叙事同创共生之后,作为一个难得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开放文本本身所拥有的价值和意义。

诚然,从小说原著到网络剧集和影片文本,敏感主体与系统暴力的存在形式和演化方式,必然是各个不同的。在小说原著里,主要人物均以亲历者身份,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依次在场并轮番发声,极为精妙地将庄德增、蒋不凡、李斐、傅东心、庄树、孙天博和赵小东七位主人公,直接询唤为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勾连的敏感主体,并使这些敏感主体与其各自不同的暴力形式体验相互关联,将来自个体迷误、人为痛苦、社会统治甚或国家机器等各种主观暴力和符号暴力,转换并展现为内在于一种更加普遍的、超客观的系统暴力,或曰神圣暴力。在此过程中,还将作为敏感主体的个体在阶级、代际、家庭、性别之间的冲突归并在一起,共同指向一个并未在场也未发声的主体:李守廉。
值得回味的是,小说中的李守廉,作为一个永远的客体和“他者”,除了在女儿李斐口中之外,总是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暴力叙事。在庄德增的讲述中,李守廉是以“小斐她爸”和“老李”的称呼出场的,“他们家哥三个,不像我是独一个,老李最小,但是两个哥哥都怕他,‘文革’那时候抢邮票,他还扎伤过人,我们也动过手,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事儿忘了”;在蒋不凡的讲述中,“严打”时期击毙“二王”的故事和市里的出租汽车劫杀案,引出的李守廉是“领着一个十二三岁女孩儿”的“中年男人”,“就在我被一片手掌大的车灯玻璃击中的瞬间,我朝那个男人站立的方向开了一枪”;而在孙天博的讲述中,转述父亲孙育新的话称李守廉为“你李叔”:“下乡之后,我们在一个堡子,他让我抓赌挣工分,有一次我和你李叔刚走到窗户边,一个小子从窗户里跳出来,想跑。我伸手一拉,他捅了我一下。你李叔马上背着我去了老马头那儿,老头用针灸封住我的脉,给我止了血,救了我一命。后来他找到那小子,把他脚筋挑断了。”

可以说,小说中始终隐身而又噤声的李守廉,才是敏感主体与系统暴力的聚焦点。主体以客体的身份,在暴力与绝望的宿命中幽灵般浮现,存在则以不在的方式,在信念与救赎的断裂处或明或灭。正是在这里,小说原著获得了一种深厚的社会/历史与哲学/神学意蕴。这既是因“叙述乐趣”而对“历史真相”的另类追求,又是对主体缺失和暴力泛在的深入批判。文本的开放确实可以创造更加丰富的敏感主体,反思更加普遍的系统暴力。在一次关于文学中的“东北”的对话中,双雪涛也谈到了这一点:“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包括在读者内部产生的再创造再联想再思考,是一个共同创作的过程,我觉得是很有乐趣的。至于为什么《平原上的摩西》里没有李守廉这个‘父亲’的叙述,简单来说就是写不下了,因为我已经写了那么多声音,在这些声音里,他已经被叙述出来了。其实,当我写到第四、第五个人物时,就已经决定放弃李守廉作为叙述者的声音,虽然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我对他的内心世界可能都不了解,觉得挺神秘的,但神秘的东西就交给神秘的空间。所以他的沉默一方面是我的无力,我没有能力把他的声音写好;另一方面,他是一个不用说话就可以塑造的人物,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读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阅读感受去思考、想象、丰富他。”[7]
对于小说文本的开放性,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也做过较有特点的解读。王德威认为,《平原上的摩西》采取多重视角,切入20世纪末铁西区工人下岗的前因后果,故事缘起则上溯至“文革”时期;人物包括转业成功的企业家、改行的出租车司机、意外受伤瘸腿的女孩、寻凶办案的老少两辈刑警,以及一位研读《摩西五经》的母亲等;故事的重心则围绕一件让东北人心惶惶的连环抢劫凶杀案以及阴错阳差的缉捕和无从挽回的悲剧后果展开。除了分析小说的故事层与主题层之外,王德威还探讨了双雪涛小说里的“艳粉街”。他指出:“龙蛇混杂,层层叠叠的棚户安置着千百社会底层生命。在居民的嘈杂和喧嚣中,双雪涛感受到他们难言的隐痛,以及由此而生的隐喻。堕落和痛苦能有什么样的救济?当暴力缓慢地渗入生存底线,是带来卡夫卡式的荒谬循环,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天启?艳粉街晦暗而沧桑,深处却矗立着一座老教堂,光明堂。”[8]在“诗意显现,神性乍生”的判断中,是批评者与创作者之间同气相应、同声相求般的深层互动。

作为视听载体的网络剧集和电影作品,尽管并不排斥小说原著的第一人称叙述,却无法让主要人物尤其焦点人物始终缺席,或者完全隐身和噤声。只有在屏幕或银幕上保持在场,敏感主体才能在与其他主体和观众的交流中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和身份。正因为如此,张大磊编导的网络剧集《平原上的摩西》,实验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小说改编法和悬疑剧叙事,不仅将小说原著中多人各自讲述的限制性的“叙述乐趣”,转变成一般影视剧最为常见的全知全能视角,而且将沈阳铁西区和艳粉街挪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普通小区。在日常平视的摄影机机位、近乎生活流的剪辑画面与不露痕迹的影像风格中,跟20世纪末的“东北”一起弱化以至消失的,除了独特多样的敏感主体之外,还有弥漫在废旧破败老工业区的一种暴力氛围。小说原著里的“文革”“下乡”“严打”“下岗潮”等各种蕴含暴力的情节因子,大都湮没不彰。诚然,相对温暖的文艺情怀、诗意的怀旧美学与悠长的韵律感,在弱化犯罪悬疑侦破情节的同时,几乎将原著改编成一部“充满年代感的青春回忆录”,[9]但在某种程度上,该网络剧集仍然没有真正放弃对敏感主体的特殊关注和对系统暴力的间接呈现。尽管在第六集亦即最后一集中,暴力发生的真相,是通过在湖中约见的庄树和李斐两人之间的对话得以揭示的;而从湖岸上警察枪口中射向李斐的子弹,更是将对小说原著里施加于各人身心的系统暴力,直接转换成一种为社会体制所接纳和容许的权力机制。在这里,敏感主体所遭遇的取消困境和阉割恐惧,跟被淡化或删减的集体记忆和个人创伤相伴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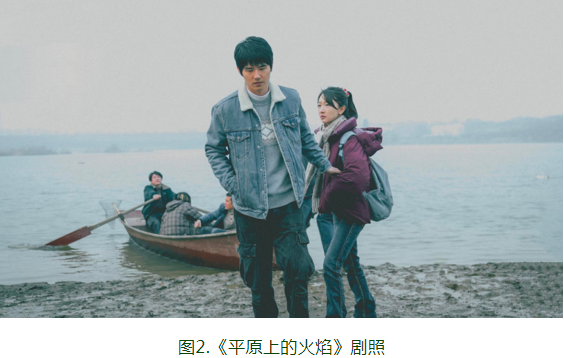
当《平原上的摩西》演变成《平原上的火焰》之后,银幕上的敏感主体与系统暴力试图回到“东北”,回到小说原著的部分设定。这个破败的东北工业小城,也开始重新被笼罩了一种冷峻、寥落和肃杀的氛围。这个由旧厂、废墟、宿舍、街道、河流、土路、玉米地、出租车、舞厅、诊所和警察局等特定空间所界定的“东北”,承载并见证着总在遭受各种暴力侵袭的无数底层个体的压抑和绝望,也是跟李斐总想前往的“南方”格格不入的一种在场。在这样的空间里,影片通过叙事焦点从李守廉向李斐和庄树的转换,构建了一对相爱相杀的、共生的敏感主体,这也使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疏离其原初的作者性及其神性和诗性,成为一部倾向于依赖小说IP和明星CP召唤普通观众的“罪爱电影”。
基于“罪爱电影”这一类型期待,在李斐和庄树的特殊关系中,饰演者周冬雨和刘昊然的搭档组合,应该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适应。相反,两人少年时代关于“火焰约定”的浪漫想象,阴错阳差地成为成年后出租车连环杀人案的犯罪线索,并最终酿成惊心动魄的“癫狂反杀”和令人愕然的“相杀相爱”。这种宿命般的人生轨迹和情感纽带,跟东北工业凋敝及其带来的下岗潮联系在一起,在强化闹事、打人和各种犯罪带来的暴力动机之时,也间接地回答了电影海报提出的问题:为何“恨一场”?如何“狠一次”?何必如此“锋利”?
暴力是暴力的根源,也是敏感主体努力克服自身异化、试图恢复个体感知的狂暴表演。在影片中,那个沾满鲜血的机械夹子按着电话号码键的镜头,虽然会给观众留下一种很难接受的强烈的感官刺激,但《平原上的火焰》最终讲述的,与其说是一个有关“爱”与“罪”的暴力故事,不如说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悲凉难耐的集体记忆与不可疗愈的个体创伤,是梦想出走而无力挣脱、屡屡被伤害终将以命相搏的底层女性的命运。平原上的火焰,既是对暴力的复刻,也是对光明和希望的召唤。影片通过既“恨”又“狠”的表达,完成了电影对小说的转译,这是“罪爱电影”的一次锐猛探索,也是国产电影在现有体制机制下寻求多方对话的一次突围尝试。当双雪涛说电影版“利索坦荡”的时候,《平原上的火焰》确实是用电影本身的方式,延续了小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