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俊蕾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
提要:影片《酱园弄·悬案》基于真实历史案件,在导演陈可辛的改编下吸引了超出常规数量的明星参演。就成片效果而言,部分表演段落风格断层,场景空间有隔断感。一方面,暴力化视听语言过多地占据了影像叙事,导致影片中意图呈现的思想议题未能得到合适的影像承载;另一方面,原本有望实现影片社会价值的公共话语打造,也因为群像人物表演的符号化和背景化而流于口号的重复。
关键词:陈可辛 暴力化视听语言 公共话语攻势 影像承载 思想议题
在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导演陈可辛携一众演员登台,用现场的舞台表演呼应大银幕画面剪辑,意图使用虚实穿插、影戏结合、真伪莫辨、多元交织的混搭风格,来介绍开幕影片《酱园弄·悬案》。接下来,也正如主创在台上用力拗准沪语发音那样,一连串的熟悉面孔密集闪现在不足100分钟的紧凑时长里。据导演的映后自述:这次拍摄一共有26位明星演员进组,进组后待的时间也不一样,“有些人来五天八天,每天都有人进出”。正当看片的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因为明星档期难调,造成了影片中影像叙事频频出现衔接障碍的时候,导演进一步道出了苦衷:“每个人都要使他们舒服,使他们习惯,使他们能够进入状态,那一进入状态没多久,他已经走了,第二个又来了······”
院线电影制作,尤其像《酱园弄·悬案》这样取材于真实历史疑案,且自带社会批判意识和两性问题反思的犯罪类型剧情片,全明星阵容的出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影片,又在哪些方面因为阻碍了艺术特有的整体性原则而对影片造成隐蔽却深刻的拖累?换言之,影片需要在哪些结构和点位上做出更加有创意、出效果的强力配置,以避免将一场悲苦残酷的民国奇案,降格、改装为博流量的明星粉丝见面会?而且,反复通观全片后可以更清楚地发现,如果仅仅止步于明星有利于吸引观众购票观看的影片工具论认知,则有可能造成表意单一的刻奇化情节虚饰,看似强化,其实浅化,甚至辜负了案件原型人物的命运之苦。那些围绕人物塑造而大量精心设置复原的空间物像,甚至是街景布置等,都连带地出现了视觉膨胀而实意缩减的悖论。即使能在短暂的场景冲突设计中虚增效果,也在根本上难以回应案件发生前后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观念走向。
作为A类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影片,[1]该项目的制作规模已经达到电影工业级别,出演阵容更是超乎一般的全明星配置,因此所要肩负的责任更为深远和沉重:既需要在当下真正承担起吸引大众消费、繁荣电影市场的文化责任,也需要如其在影片中所高声宣示的那样——实现民智启蒙的社会功能,关注性别议题,鼓励女性自我觉醒并推动两性平等的普遍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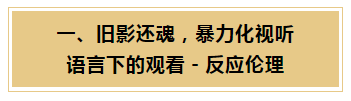
“杀夫”故事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睡梦中被剪去头发而消失了神力的古希腊大力士安泰,在传说中就是遭到了枕边人的暗算。相较而言,酱园弄案件因家暴而愤起,更倾向于“警世恒言”类型的市井公案。细究起来,章子怡饰演的詹周氏,在以弱克强的杀人反抗行为上,近似于1934年导演吴永刚拍摄的《神女》;其在庭审后愤愤不肯屈服的台词“我要活”,更是直接回响了1935年导演蔡楚生拍摄的《新女性》话语。阮玲玉在两部影片中的角色残影,仿佛穿越了岁月,在同主题叙事中隐约浮现。20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电影,在一个放大了暴力表现,又不断追加悬念感的罪案叙事中还魂而来。
落后的社会制度往往造成并姑息着畸形的家庭伦理关系。在男权不被反思、法律制度也需要完善的时代,一旦有女性人物不幸处于异性的权力掌控之下,可供其选择的出路已然少之又少。除了娜拉出走命题所提供的堕落与返家两种窒息操作外,基本上只有“反杀”才可以自救或自保。《神女》中的母亲和《酱园弄·悬案》中的詹周氏在面对烂赌成性、勒索无度的男性对头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暴制暴”的戏剧化解决方式。所不同的是影片赖以推进情节表现的视听语言,以及相应的观看-反应心理机制。《神女》采用了传统东方式的苦情哀歌,将重点集中在阮玲玉的面部表情上,依靠细微传神的情绪表情变化,进行情感化的故事讲述;再通过字幕插入,进一步激发观众的同情和共鸣;最终通过片中理想化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的无私帮助,唤醒社会良知,在点到即止的暴力表现和象征性的权力构图中建立矛盾冲突,又在温情的同理心表达中实现影片的社会教化功能。然而,同样在弄堂空间里发生的詹周氏杀夫案,《酱园弄·悬案》却在陈可辛导演的电影上半部“悬案”中一再延宕,为的是抓住每一个能够添加恶行暴力的剧情点,加大影像叙事的暴虐感。
为了放大画面的暴力感,影片编剧不惜将疑案表现的情节重点,从查案破案的智性逻辑思维和攻心为上的心理意志攻势,生硬地转变为直达人物身体的私刑滥用。雷佳音饰演的警察局长薛至武,与其说是一名执著于破解悬案的日伪政府公职人员,不如说是詹周氏刀下亡魂的另一个化身。影片中,每次他与詹周氏会面,都会解锁一种新的施暴形式,从拳打脚踢扇耳光,升级为放猪追咬,甚至是含血喷人、假造物证、罗织罪名、严刑逼供,并且罔顾常识,漠视真相、不顾民心民意,一味刚愎自用地维护可悲可笑的自我权威与尊严。直到影片行将结束,眼看詹周氏要因为政权更迭而逃出自己的掌控,竟然不管不顾地擅自驾车闯入女子监狱,对詹周氏拔枪相向。宁可冒着自己被新进城的队伍俘获的风险,也要先一枪了结詹周氏的性命再说。这样一个亡魂残影般的矛盾结合体,既不能说他断案认真,因为他只草草勘察一圈现场就下了主观定论;也不能说他办案不认真,因为他把所有的气力都倾注在如何迫使詹周氏低头认罪的想法上,哪怕时局动荡,连他自己都已经朝不保夕,却始终不肯放詹周氏一条生路,阻拦她趁战乱动荡而侥幸逃脱杀夫罪责。
有不少观众发现,薛至武与詹周氏二人间的复杂张力关系远远超出了查证凶案的常见模式。此中深意显然是有意为之,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掘旧案题材在当下思想场域中的翻改意义,另一方面也给影片中的人物动作提供了更大的表现幅度,在运动画面的激烈震荡中进一步强化视听刺激。影片以审讯为情节主线,在暴虐私刑和公开庭审之间展开拉锯战。其中一场突出动物元素的设计更是匪夷所思,让一头疯癫狂躁的黑色大肥猪去追逐、撕咬詹周氏。[2]囚笼底部是黑猪,在上方踱步的薛至武投下他的黑色身影。人的黑影交错叠加在猪的身上,其中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在詹周氏的心理闪回画面中,又反复出现对她非打即骂的丈夫,同样是以压迫性的、自高而下的倾斜俯视视角逼近过来。在詹周氏的紧张幻觉作用下,从她一直被摄影机俯拍的视角望上去,被杀的丈夫“大块头”与暴力办案的警局薛局长在形象上时有叠合。前者仿佛阴魂不散,后者犹如恶灵附体,构成了一组互为对应的施暴者,不分过去或现在、私权或公权、熟悉或陌生。当詹周氏被这无法逃脱的残暴蛮力虐待到无路可逃、无望可盼的绝境时,她主动地选择了决绝一跃,宁可被牲畜践踏,也不愿继续忍受来自同属人类的无休止欺凌。
对于国民性的幽暗成分,鲁迅先生曾用“瞒和骗”加以概括,批判那些色厉内荏的懦夫,因为不敢正视现实,所以自欺欺人,更兼害人害己。影片中,“大块头”将赌瘾难戒的责任推脱到詹周氏身上——“不赌,我拿什么养你?”薛局长则一次次诱骗詹周氏,在道德上羞辱她,在智力上轻视她,在一次次不能得逞之后变得更加愚蠢而疯狂,似乎失去了头脑一般,由此与凶案中失去头颅的亡夫“大块头”继续构成形象虚实之间的异形同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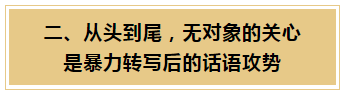
就案件原型的庭审记载来看,实际罪行确实包含砍杀后的肢解。但在肢解后留在现场的16块人体片段清点中,不仅没有失去头的影踪,而且是“头胸一段”。没有藏头、抛头的额外花头,更没有所谓请神做法、斩断孽缘的故弄玄虚。虚构人物宋瞎子的台词也就无从说起,譬如“命恨姻缘不到头,此生空余断弦愁”,譬如“长官你属鸡,詹周氏属兔,为‘六冲’”,以及看似劝阻其实更加拱火的建议——“这案子你别碰!”
上述台词在脱离偶像明星的表演后益发显出怪诞与空虚,侧面说明:该片改编在人为制造薛至武与詹周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所依靠的合理因素非常有限。造成这一有限性的原因,既在于大量明星参演,各自成就精彩表演段落,也在于将原本头尾相连的完整剧情肢解得七零八落。薛与詹之间的对手戏因此落入了一见面就剑拔弩张、分开后就没有了任何关联的奇怪状态。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影片的空间调度上:弄堂、赌坊、法庭、女子监狱,以及偶然闪过的当铺内景和暴雨下的苏州河外景,横跨了十年记忆的叙事空间如同遭到了同样暴力的肢解,线索散落,段落间彼此隔离,没有做到自然完整的头尾衔接。
此间的悖论在于,随着主题设定与事实表达渐行渐远,电影中的物像准备越丰富,所能够呈现的人物面目反而越雕琢。在这一桩牵涉真实生死的杀夫命案中,每当影片叙事即将触及事件真相和人物内心,往往会习惯性地拉扯上两性话题,甚至台词也暗示性地表达战争走势和民族大义等。从口号式的音画分离,发展为分贝剧增的众声喧哗。那些跟随女作家西林(赵丽颖饰)一起呐喊“不屈服”口号的庭审观众,以及在监牢里跟随女牢头王许梅(杨幂饰)一起合唱《梁祝·十八相送》的囚犯们,无非是没有姓名,也没有面目的人形背景板。她们只有在情节需要的时候,才暂时地被笼罩在镜头里面。当镜头大量地聚焦在明星演员的脸部和他们身形周围的小空间时,这些数量庞大的背景人群,自动地调成了噤声模式,静止在焦点虚化的中远景部分。按照导演的说法,《酱园弄·悬案》“塑造了一帮群像人物”。在群像人物的背后,还陪衬有更大数量的背景人群。在暴力施虐转写为话语压力的情节策略下,这些人群的言行真正影响着叙事的节奏,也是影片《酱园弄·悬案》有可能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在一个话语昌明的市民社会,来自公众舆论的良知与共情,可以救人性命,也可以警醒并防止职权滥用的行为。其前提条件在于,关心真正的人,真正做到重现人物的情感逻辑与行为动因,并从中自然涌现出有意义的社会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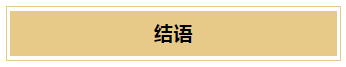
在这个意义上,《酱园弄·悬案》表现出一个值得深入辨析的共性难题。对于包含社会议题的历史题材电影而言,影像叙事究竟是贴近真相与原貌的现实主义摄像头,还是可以恣意放大感官刺激、调高视听语言反应的情绪传感器?导演陈可辛没有按照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论做出排他性选择,而是努力在理解上海文化的历史基础上进行影像表达,始终将詹周氏一案的起伏变化置于大众观看的公共视野场域内。从片头宋瞎子满脸淌血被丁字路口的汹涌人潮围观开始,詹周氏的案情与案发前的镜头闪回,交相展现在“看客”与“观众”的不同视阈中。
赌徒丈夫恨她干涉自己在赌场上的快活,于是,一边暴打、一边拖拽她的头发,拖下台阶,再重重地摔在四周都是食客的场院里。影片在此处接上了几个环境镜头,少数食客不忍看到被打的场面,扭过脸去,或者挪动自己的座位,避免被牵连;更多的画面则表现了食客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视若无睹,还在自顾自地搛菜入口,丝毫不影响用餐速度和胃口。这些简洁的画面隐含着鲁迅对于看客群像的讽刺与剖析:冷漠而麻木地将自己间隔于事件之外,丝毫不做自我责任感的体识。
十年婚姻被凶案画上句号之后,围绕詹周氏的抓捕、送审、判罚,以及当庭翻供、再送审和再判罚······每一次都集聚了大量的围观者,填满整张大银幕的画幅。而且,这些围观者不再是沉默无言的看客,相反,他们成为影片声场的实际发出者。新闻记者挤在楼梯两侧,追问薛至武破案细节并暗讽他的无能,后又聚集在法庭前追问无头悬案的进展。法庭仓促判罪后,旁听席上的观众附和西林的口号,齐声鼓励詹周氏抗诉。这些大合唱般的声音在影像叙事中固然生硬有余、生动不足,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导演陈可辛在影片创作上的思想坚持。即便受累于众多明星参演带来的风格断层,他依旧想在旧案翻拍的再创作中生发新意;即便在个别画面构图与音乐节奏上,部分再现了四十年前台湾地区同题材电影《杀夫》的设计,陈可辛也坚持在个体空间的行为暴力与公共空间的舆论话语之间进行新的因果逻辑连接。眼下之所以没有在影片上半部的“悬案”讲述中完全实现创作意图,主要原因在于思想议题的影像承载与事件本身存在脱节,附带说明了暴力化场面不足以依恃。或许在未来上映的《酱园弄》下半部中,影像重点回归事件本身,关心真正的人,承认人不仅有躯体,更有灵魂,在新老律师联袂登场的新语境下,创作出内核感人、头尾相连的完整故事。